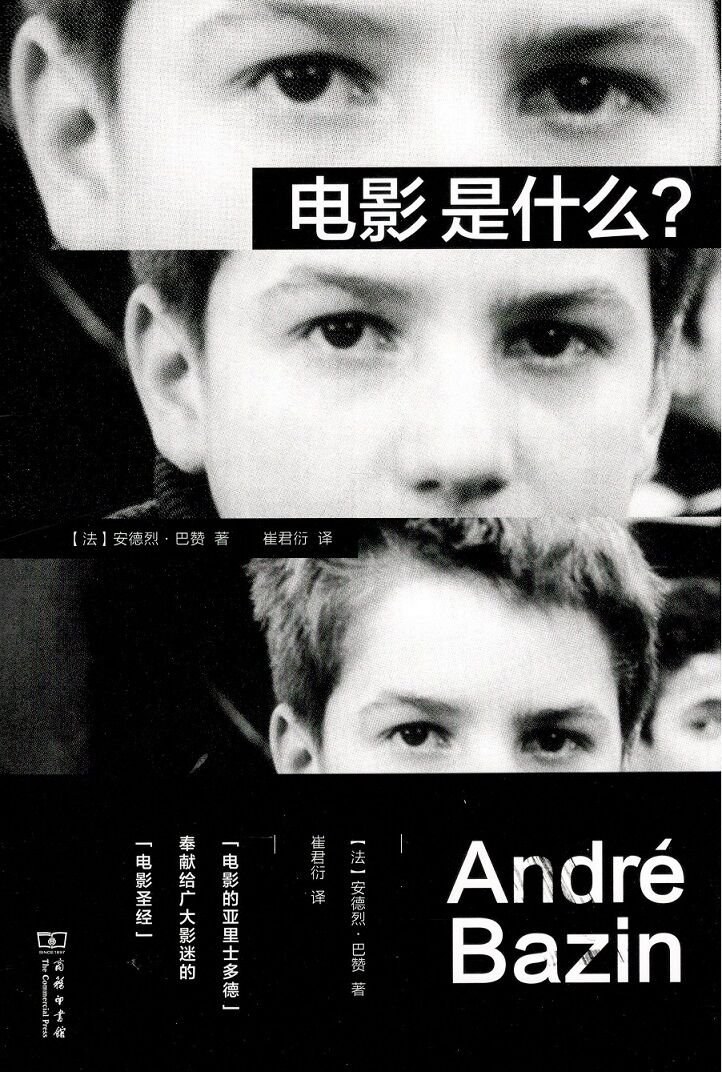
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包含一系列短小精悍的议论文章和影评,在上新一轮导论课的当口,反复阅读了前两篇立论雄文,发点笔记上来。
在探讨摄影术的文章《摄影影像的本体论》中,巴赞首先指出,像木乃伊一样封存人类外形、抗衡时间以获得永恒的追求自古有之,也是绘画与雕刻等造型艺术的起源。此后的造型艺术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是记录外在现实,即一种追求形似的心理愿望;另一条是表达精神现实,即一种象征主义的美学追求。在中世纪以前的艺术作品中,两条路径没有明显冲突。然而,文艺复兴时期引入的透视画法,作为一种初具机械特性的新技术手段,使画家开始致力于在画布上还原三维世界的真实场景,以至于对现实幻象的心理追求扰乱了造型艺术的抽象美学追求,文中称之为一种“原罪”。直到摄影术诞生,使自然景物可以用一种纯机械式的、没有人工干预的、决定论的方法记录下来,完全满足了“将人排除在外,单靠机械复制来制造幻象”的欲望,这才把艺术家从追求形似的执念中解放出来,使其可以专注地追求艺术本体,从而催生了印象派等“摆脱现实主义纠缠”的新流派。同时,照相机的普及也使忠实还原现实的权力与情结都下放到普罗大众手中。巴赞强调,“摄影与绘画不同,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摄影不是像艺术那样去创造永恒,它只是给时间涂上香料,使时间免于自身的腐朽。”基于这种观点,电影的出现在时间维度上进一步完善了摄影术的客观性,让被摄物从静止的琥珀状态变为运动状态,仿佛木乃伊动了起来。这里提到,超现实主义流派反倒会使用摄影术作为创作媒介,因为摄影取得的影像具有自然属性,是自然造物的补充而非替代品,能够展现幻象的本质。
在接下来的《“完整电影”的神话》中,巴赞遵循乔治·萨杜尔《电影的发明》的脉络,重新审视了电影的前史,并探讨了技术进步与电影诞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业进步与心理学发展的相互影响。他认为,并不是技术进步催生了新的艺术形式,而是人们早已有了对“全面记录现实世界形象、声音、运动、立体感”的“完整电影(cinéma total)”的追求,或曰一种神话式的畅想,但受限于当时的工业和技术发展水平而不能实现。技术发展是跟在观念之后的,是观念的一种实现形式。基于这一前提,巴赞又探讨了为什么普拉托(诡盘)、慕布里奇/马莱(连续运动照相)等研究者仅满足于连续记录或呈现影像这一目标本身,没有直接催生电影的发明;而电影先驱爱迪生和卢米埃尔也因商业模式的局限性,仅将雏形阶段的电影当成一种玩具,没有进一步推动电影艺术和产业的发展。(原文:照相式电影在必不可少的技术条件尚未完备之前便已出现确实令人惊叹,但是我们仍应该解释清楚,为什么在一切条件久已具备的前提下(视觉暂留是自古已知的现象),人们竟隔了这么久才开始发明电影?)巴赞的结论是,上述先驱都是实干为主的发明家,不是“耽于幻想的妄想家”,因此他们受制于时代的想象与思维的局限性,止步于自身设计的目标。所谓“完整电影”的终极梦想存在于那些幻想家的脑中,要等待技术的进步让这些幻想一步步落实。文末给出一个形象的比喻:“伊卡洛斯的古老神话要等到内燃机发明出来才能走下柏拉图的天国。但是,每个人从第一次观察飞鸟时起,这个神话就蕴藏在心中。”
关于“完整电影”, 巴赞认为,电影的终极追求就是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也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一应俱全的外在世界的幻景。因此,电影是人类追求逼真地复制现实的心理产物。他驳斥了认为有声片和彩色片折损电影质量的观点,赞许了这些使电影本体一步步接近“完整电影”的技术革新,并认为“一切使电影臻于完美的做法都无非是使电影接近它的起源”。引用文中激情澎湃的论述:“支配电影发明的神话,就是实现隐隐约约地左右着19世纪从照相术到留声机的一切机械复现现实技术的神话。这是完整的现实主义的神话,这是再现世界原貌的神话,影像上不再出现艺术家随意处理的痕迹,影像也不再受时间不可逆性的影响。如果说,电影在自己的摇篮时期还没有未来’完整电影’的一切特征,这也是出于无奈,只因为它的守护女神在技术上还力不从心。”
《电影是什么》之后的篇章开始从巴赞的影像本体论过渡到电影美学,他认为真实性是电影语言的演进方向,电影的整体性要求保持事件空间的统一和时间的真实延续,因此他认可以长镜头和景深镜头为代表的美学取向。不过仅从前两篇立论就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巴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技术乐观派,他的影像本体论可以说是唯心的,甚至带着宗教情怀的。这样的观点想必会遭到不少反驳,但作为技术相关的从业者完全能够感同身受。如果他活到现在,对种种新出现的沉浸式技术想必也会赞许有加。
转载请注明来源。欢迎留言评论,欢迎对文章中的引用来源进行考证,欢迎指出任何有错误或不够清晰的表达。